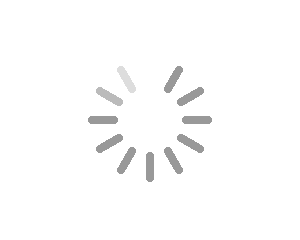袁世凯窃取革命果实后,下令强制解散女子参政同盟,高涨的革命热情陷入低谷,女子参政同盟星散,王昌国全心转入自己一手创办的中央女子学校的教学和管理工作,张汉英则回了醴陵,在自己多年前创办的醴陵女子学堂改组的醴陵县立女校任教,课堂上仍不忘向学生宣扬男女平等的女权观点,惹得一帮守旧的腐儒顽绅大为火光,四处诋毁,最可唏嘘的是,与自己志同道合的革命伴侣李发群参加反袁的二次革命,因叛徒出卖被捕,被张勋枪杀于南京……忧思重重,又兼教学任务重,本就身体不大好的张汉英被病魔击倒,于1916年咯血而亡,终年四十四岁。顺带一提,张汉英婚后多年未育,丈夫李发群在南京曾纳闵姓女子为妾,有遗腹子一,牺牲后由闵氏老母伴送回醴抚养,汉英喜夫家后继有人,视如己出,课余回家精心照顾,相依为命,对闵太夫人亦恭礼如生母。这好像与张汉英等一直宣扬的男女平权之理念相抵牾,其实也无需苛责,数千年来的封建礼教束缚远非朝夕间便能祛除干净,这种矛盾,或者说挣扎,正是张汉英那一代首次发出“男女平等”宣言的中国进步女性必须经历的转型阵痛,即便如此,也无损于其在中国女权运动史上的巨大贡献。
王昌国赠送给友人的墨盒,时在1922年,当为其参选议员期间所制。
现在轮到回头说说王昌国的壮举了。上世纪20年代初期,湖南掀起一场全国瞩目的“联省自治”运动,颁布了中国第一个省级宪法——《湖南省宪法》,并将女子参政权正式写入宪法,这比十余年前的颁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高明了不止一星半点,尽管从日后的发展形势看,这部《湖南省宪法》仅仅具有文本上的意义,从未落到实处。远在北京的王昌国闻知消息,决定回乡参加竞选,哪晓得尽管宪法明文规定女子有参政之权,醴陵官绅把持的地方选举委员会却不肯将选票分与女选民,惹得女届代表抗议,双方大打出手,致7名女子学校的女生被殴伤。王昌国等乃集合千余人到醴陵县署力争,“三日不食,夜则露坐庭中。外间复时以危言恐吓,谓男界将不利于女子,女界屹不为动。县校女生尤告奋勇,每人手握一纸,书写自愿打死字样,谓如果有不测,各家长不得埋怨,校长教员亦未加阻止……”眼见事情闹大,不好收场,县署方面也只得妥协,“乃与区境董协商,准如所请。”醴陵女界以如此激烈的方式推动选举,引得益阳、宁乡、湘潭、衡阳等县女界争相效仿,大争女权。最后王昌国成功当选醴陵县议员和湖南省议员,妇女界如愿以偿,王昌国也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女性省议员。
轰轰烈烈的湖南“联省自治”运动很快在军阀混战中落幕,王昌国重新转向教育,担任长沙务本学校校长,直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乃回醴陵夫家定居,不再参加社会活动,于1954年病逝,但其参选议员的经历却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为女性争权利者的坚定信念——权利,从来不是上方施舍给你的,而须经过流汗流血的抗争而来。
肆
“各党人一一依判决名次点名,宣告执行,由执刑吏及兵警送往绞刑台。闻看守所中内有绞刑台两架,故同时仅能执行二人,而每人约费时18分钟绝命。计自2时至5时,20人始处刑完毕,首登绞刑台者为李大钊,闻李神色未变,从容就死……行刑既毕,尸身20具并列于绞台之侧,男尸19具,女尸1具即张挹兰也。”
就义前的李大钊(中)、路友于(左)和张挹兰(右)合影。
1927年4月28日下午1时许,奉系军阀张作霖控制的北京安国政府以“宣传赤化、主张共产”等罪名判处李大钊等20名进步人士死刑,次日出版的《申报》以《军法会审昨日开庭,判决党人二十名死刑》为题,详尽报道了本次荒唐的审判以及行刑的大致经过。
作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国人对李大钊就义前后的种种可谓了然于心,相较而言,与李大钊同上绞刑架的另外19名进步人士就所知甚少了,尤其是其中唯一的女性张挹兰。
张挹兰,1893年春出生在醴陵西乡一个没落的“书香之家”,祖父是前清秀才,在家中开有私塾,不过在彼时的舆论氛围下,女子是没资格进入学堂学习的,醴陵最早的女子学堂还要等到1906年回国的张汉英来创办。好在祖父相对开明,耐不住幼小的张挹兰软磨硬缠,答应在每日私塾放学后教她读书识字,聪明好学的张挹兰埋首于书本,刻苦钻研,不过数年间,便成长为能写会算、远近闻名的“女秀才”。
辛亥革命后,在张汉英、王昌国等妇运先驱的鼓吹下,偏于内陆一隅的醴陵也涌动着女权独立的思潮,新式学堂亦招收女生,县城甚至有了专门的女子学堂,尽管在守旧人士看来,女子抛头露面出入学堂仍属离经叛道之举。此时的张挹兰已在家人的安排下嫁人生子,又在之后不幸遭逢丧子之痛,精神上的苦闷让她急于做点什么,于是离开夫家到县城的女子学校念书,校长正是此前闹得沸沸扬扬的女子参政同盟的重要领导者张汉英,各种新思潮的洗礼极大开阔了张挹兰的眼界,也定下了张挹兰日后不遗余力为女子争权利斗争的基调。
1919年,为探求新知识,张挹兰北上京城求学,先考取了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预科,住校攻读一年后,为谋生计,又漂洋过海到到南洋的苏门答腊首府棉兰的华侨学校当老师。在南洋教书期间,张挹兰深感自己知识的欠缺,一年之后,又重返北京,考入北京大学预科继续学习。
1924年,张挹兰升入北大教育系学习。此时,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在苏联和中共的帮助下实现了改组,随即国民革命运动兴起。由于北洋军阀统治内部内讧不断带来的权力松弛,北京的革命形势渐趋高涨,而北大又是北京的革命中心。张挹兰在北大结识了李大钊等革命进步人士,更与湖南同乡、中国共产党第一位女党员缪伯英结为好友。受他们的影响,张挹兰逐步改变了原先的“教育救国”的思想,开始热情地投身于大革命运动,即反帝、反封建、反军阀的革命斗争。1925年4月,张挹兰加入了国民党左派组织中山主义实践社,并加入国共合作的国民党,后当选为中山主义实践社的理事。
1926年三一八惨案后,北京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以李大钊为首的中共北方区党委的领导机关转入地下。为保存革命力量,继续开展工作,3月底,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共合作组织——国民党北京执行部和北京特别市党部,由翠花胡同8号搬到东交民巷苏联大使馆西院旧俄国兵营办公。4月,北京特别市党部再次进行改组,张挹兰当选为执行委员。为了进一步开展妇女运动,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决定在北京办一个妇女刊物《妇女之友》和一所职业学校缦云女校,作为妇女运动的阵地,张挹兰出任《妇女之友》主编和缦云女校校长,中共指派韩桂琴(即韩幽桐,张友渔夫人)担任《妇女之友》的副主编(一说编辑部副主任),他们的共同上级,正是张挹兰的挚友、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周恩来同志的入党介绍人、时任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妇女部部长的刘清扬。
出任《妇女之友》主编期间,张挹兰编发了大量呼吁妇女解放的文章,还亲自动笔撰写了诸如《妇女运动述略》《新妇女的使命》之类的重头文章,不仅对身受多重压迫的妇女同胞表示同情,还号召广大妇女勇敢地参加救国运动,和全国人民团结一道,铲除国贼,抵抗列强,扫除旧社会的陋习,靠自己的努力换取平等的地位。显然,这样的呼吁比之张汉英、王昌国等前辈乡贤的主张又进了一步,不再只谋妇女个体的独立解放,而转而为国家、民族的独立解放鼓与呼,作为张挹兰投身妇女解放运动的第一个老师,想必九泉之下的张汉英也会颔首肯定的吧。
相比这些理论大块头,个人其实更推崇张挹兰写的那些有关妇女新生活的科普类小短文,如刊于《新文化》创刊号上的《母爱之调节与其要点》一文,这是她应自己北大的老师、《新文化》主编张竞生先生之约撰写的。在这篇文章中,张挹兰提出了要“实行生育节制”的主张,还列举了避孕的多种措施,她认为这是解放妇女的迫切之举,文末更是提出“我希望今日之母亲,对于儿女开导性欲的责任,应与饮食住供给一样平视”,鲜见地将如今都有些讳莫如深的青少年性教育问题付诸笔端,自然惹得一帮“卫道君子”的口诛笔伐,连带刊载这篇文章的《新文化》杂志,也被彼时不少媒体批评为“宣传淫行”。可张挹兰仍是不管不顾,继续在繁忙的工作之余,撰写类似的有关妇女生活方式的科普小短文,或许在她看来,争妇女解放这个话题过于宏大叙事,在女子普遍受教育程度不高的彼时,难以骤收奇效,而这些类似避孕、青少年性教育之类的科普短文,则可以实打实地帮助彼时的女性从不能发声的生育机器中解放出来,逐步拥抱相对进步的新的生活方式,革命嘛,两条腿走路,既需要摧枯拉朽的暴风骤雨,也需要润物无声般的潜移默化,一个都不能少。
1927年3月,刘清扬奉调到武汉国民政府工作,张挹兰接任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妇女部部长之职,肩负起领导整个北京妇女运动的重任。刘清扬离开北京前,曾跟李大钊密谈,是否再次考虑吸收张挹兰加入中国共产党,李大钊自然清楚自己这个学生的为人,也早就将其列入发展党员的名单之中,只是当时形势复杂,出于慎重的考虑,没有立时答复,希望她能在严酷的斗争中接受进一步锻炼和考验。
1927年4月6日清晨,反动军阀警察闯入张挹兰的家中,将其逮捕,几乎同时,李大钊亦在家中被捕。被捕后的张挹兰被反动军阀多次审讯和逼供,敌人妄图从她嘴里挖出更多的秘密,这个编外共产党员却难能可贵地保持了中国共产党党员一贯的高尚情操,始终守口如瓶,没有吐露半点机密,也没有使任何同志受到牵连,保持了革命的气节。
4月28日,反动军阀突然对李大钊、张挹兰等二十位革命党人进行紧急“宣判”,判处李大钊、张挹兰等绞刑立即执行。这场荒唐的审判,从开庭到结束,仅仅用了两个小时,宣判结束后,李大钊、张挹兰等就被押赴刑场,于是便有了本节开头的那一幕。
张挹兰牺牲后,其遗作《关于庚款用途的一些建议》刊于5月号的《新文化》杂志,洋洋洒洒数千字,都是建议用退款发展国家文教事业,老师张竞生并撰《哀女生张挹兰》一文附后,称张挹兰之死“可与古罗马争取共和的女英烈露克尼丝和清末的秋瑾烈士媲美!”
从争女性个体之自由到争国家、民族之解放,并为之献出生命,张挹兰并非孤例,在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时期,无数优秀的“巾帼不让须眉”的株洲女性为国家之独立、民族之解放挺身而出,抛洒头颅热血,她们包括但不限于在领取情报时被抓却始终不肯透露机密,而被敌人残忍杀害的年仅15岁的攸县女英雄张秋英,创办茶陵第一所女子学校并带领女学生积极参与革命行动而被杀害的妇运先驱谭道瑛,积极参与农运又隐藏身份为红军提供军事情报不幸被捕受尽酷刑始终不屈的革命烈士汪起凤……恕我不能将名单一一开列下去,在为民族求解放、为国家争独立的路上,株洲女性的付出与牺牲从未落过下风,据相关资料统计,仅茶陵一地,大革命时期牺牲的有名有姓的烈士名录便有259人。
伍
弯弯曲曲的乡间小道上,独轮车碾过吱吱嘎嘎的声响打破了春日的宁静。推车的汉子一副常见的农人打扮,面色黧黑,嘴唇紧闭,显得朴厚而沉稳,车上是一银发幡然的老太太,并有两只硕大的木箱和一卷乡间并不常见的制式被卷。
袁昌英。
这是1970年的初春,头戴“极右分子”和“历史反革命”两顶帽子的武汉大学原外文系教授袁昌英被学校限令离校,在“五七”干校改造的女儿杨静远好容易联系上母亲老家的远亲袁星山,将其安送回老家醴陵落户,这位离家数十年的游子终于在人生的暮年得以重返生养她的这片山水之间,尽管理由不是那么体面。
于熟谙中国近、现代文学史的人来说,袁昌英绝对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名字,这位中国第一位留英女硕士,也是第一个将莎士比亚戏剧绍介引进至大学课堂的女学者,创作有《孔雀东南飞》《活诗人》《究竟谁是扫帚星》《人之道》《结婚前的一吻》《饮马长城窟》等10多个剧本,兼长散文小说,其作品至今仍为国外多所大学治中国文学者所研究。
当然,对于彼时的她而言,这些荣耀已不是最紧要,谨言慎行才是根本。好在乡风淳朴,乡邻们只当她是远游归来的老家亲戚,嘘寒问暖间也尽是久远的家族往事,这多少